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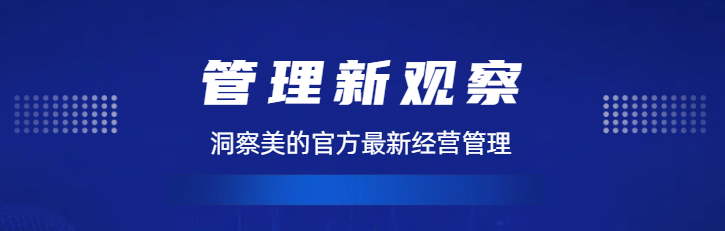
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中国经济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。机遇与挑战并存,希望与困难同在。在这个时代的关键节点上,我们既要正视眼前的重重矛盾,也要洞察矛盾背后蕴含的深层逻辑与未来走向。笔者认为,未来很长一段时间,中国经济将存在以下五大困局,我们所有的人都无法绕开。一是宏观刺激不断放大与成效越来越小的困局;二是官方各种数据持续亮眼与国民体感越来越差的困局;三是居民存款越来越多与消费持续低迷降级的困局;四是企业持续追求量双收与量利双降的困局;五是知识型人才越来越多与机会越来越少的困局。

01 宏观刺激不断放大与成效越来越小的困局
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,近年来宏观政策持续发力。货币政策上,央行多次降准降息,广义货币供应量(M2)持续保持高位增长,2024年末已突破292万亿元。财政政策上也积极发力,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屡创新高。
然而,政策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。大量资金滞留于金融体系或流向安全领域,难以有效注入实体经济毛细血管。2024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(CPI)同比仅上涨0.2%,2025年以来持续低位徘徊,凸显内需疲软。
正如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·德鲁克所言:“动荡时代最大的危险不是动荡本身,而是仍然用过去的逻辑做事。”我们习惯于以加大投资、放宽信贷的“旧逻辑”应对结构性难题,其结果必然是刺激成效递减。这好比向饱和的海绵注水,纵有千钧之力,亦难再吸纳分毫。
02 官方各种数据持续亮眼与国民体感越来越差的困局
宏观数据显示,2024年中国经济保持稳健,国内生产总值(GDP)同比增长5.2%。进出口规模稳中有升,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快于全部投资。
但与宏观亮眼数据形成反差的是公众的体感“温差”。年轻人感叹“卷不动”,求职者面临“好工作难寻”的困境。这种落差源于增长成果分配与居民实际获得感之间的错位。
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·斯蒂格利茨曾指出:“如果你不能衡量你所看重的东西,那么你最终会看重你所衡量的东西。”统计数据精准捕捉了经济增长的“量”,却难以完全反映增长成果分配的“质”与居民幸福指数的“感”。当增长红利更多向资本倾斜,社会流动性放缓,宏观数据的“靓丽”与微观个体的“焦虑”便形成裂痕。
03 居民存款越来越多与消费持续低迷降级的矛盾
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引人注目:一方面,居民存款持续攀升。央行数据显示,2024年人民币存款增加25.74万亿元,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6.67万亿元。
另一方面,消费市场并未同步升温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放缓,“消费降级”现象显现,消费者更青睐拼多多等性价比平台。
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·塞勒的“心理账户”理论为此提供了解释:人们将资金归类于不同心理账户。当前储蓄增长更多源于对未来的“预防性储蓄”,存放于“安全保障”账户而非“即时消费”账户。经济前景不确定性、就业市场波动强化了避险情绪。亚马逊创始人杰夫·贝索斯曾言:“你的利润就是我的机会。”当大众紧握储蓄时,整体商业机会便在静默中收缩。
04 企业持续追求量利双收与量利双降的困局
商场中,“量利双收”是企业理想状态。然而当下许多企业却陷入“量利双降”困境。为保住市场份额,企业卷入价格战,利润空间被极致压缩。2024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.3%。
反之,若企业试图提价保利,又可能流失价格敏感客户,导致销量骤减。
投资大师查理·芒格曾幽默比喻:“如果你唯一的工具是一把锤子,那么你看待所有问题都像钉子。”许多企业过往成功的“锤子”——渠道为王、规模效应——如今已然钝化。现代管理大师克莱顿·克里斯坦森所警示的“创新者窘境”在此显现:企业受困原有模式,难以开创突破性增长曲线,最终在成本与竞争夹击下量利双失。
05 知识型人才越来越多与机会越来越少的困局
中国拥有庞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。2025年高校毕业生预计达1179万,知识型人才供给空前。
然而,匹配人才的优质岗位增长未能同步。其结果便是“内卷”加剧与“学历贬值”。硕博竞争基层岗位、海归入职街道办已非鲜见。
此矛盾根源在于经济结构转型速度滞后于教育输出。管理学家赫伯特·西蒙指出:“信息消耗的是信息接收者的注意力。” 同样,过剩劳动力消耗的是就业机会。当人工智能、生物科技等新兴产业容量尚不足以吸纳全部新增人才,而传统产业又处转型阵痛时,人才与机会错配便成必然。
结论与启示
五大矛盾如多棱镜,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至新阶段面临的深层挑战。它们相互关联,构成系统性难题。
核心启示在于,我们需告别过去粗放增长模式,从“量”的扩张转向“质”的提升。这要求我们:
深化改革,打破刺激政策边际递减,疏通经济循环堵点;
优化分配,缩小宏观数据与微观体感温差,让发展成果更公平共享;
强化保障,转变居民谨慎预期,将“超额储蓄”转化为“敢消费”的动力;
激励创新,助企业跳出低水平竞争,开辟高附加值“新蓝海”;
加速产业升级,创造更多匹配高素质人才的优质岗位。
恰如查尔斯·狄更斯在《双城记》开篇所写:“
这是最好的时代,也是最坏的时代。” 矛盾预示风险,更孕育机遇。能否穿越迷雾,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新阶段,取决于我们能否真正正视并化解这些深刻矛盾。